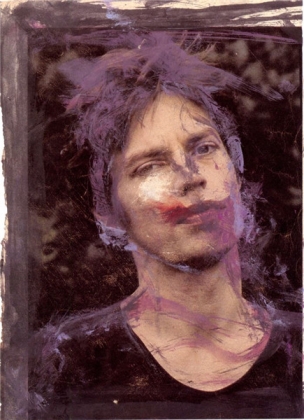


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讲,《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最关心的两种艺术形式——诗歌和绘画,在理想社会中是无立足之地的。柏拉图认为,时间万物,比如桌子、椅子,并非最终意义上的真实存在。因为它们形成,随后消失;因为它们经历着各种变化;因为它们并非其所属物系的理想代表,所以,它们缺乏不受时间限制、不经历发展变化的“形式”所具有的那种完整的真实性。我们熟知的日常事物虽存在,但它们只具有“形式”的一些品质,或者只是“形式”的一部分,它们距离亘古不变的“形式”尚有一定的距离。
柏拉图关于艺术的理论,即艺术是对模仿品的模仿,与他所提出的“形式”论密不可分(柏拉图认为音乐不是对事物的模仿,却又在其他地方指出,理想国应该只包括那些人们不想听的、不至于激起人们情感的音乐)。苏格拉底还指出,艺术创作,即绘画与诗歌,是三种存在中最不真实的一种存在,另外两种存在分别为“形式”和日常物品。因此,艺术家甚至还不如手工艺人那样更接近真实,因为后者至少会努力去复制“形式”,从而创造出日常物品,而前者则只以这些日常物品作为创作的模子,也就是说,他们实质上是在对复制品进行复制。
在“形式”论这个前提下,苏格拉底担忧的不单是艺术作品仅仅揭示表象物质的表象这个问题,他同样担忧的是,艺术作品只激发人们的情感,因而无法推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正确理解。尤其是文学(苏格拉底以诗来代表文学),苏格拉底认为它激发了人们心灵深处的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因而对它提出了批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艺术构成了对哲学的挑战,哲学虽也试图对人们施加影响,不过它是通过理性手段,而非通过感性手段进行的。因此,应该废止艺术,以确保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不受不良因素的干扰。
由此看来,作为对日场事物进行模仿的艺术,柏拉图对其提出的批评跟社会实用性有关——艺术是危险的,因为它激发人们心灵中非理性的一面,从而干扰我们对理性的合理追求。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跟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认为艺术即是模仿(即“再现”)。不过,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对整个艺术、尤其是悲剧持一种欢迎态度,它认为艺术作品并非在讲述事物真相方面与哲学展开竞争,相反,它们通过与哲学密切合作来揭示事物真相。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出精心构思的悲剧所传达的人类本性的真谛并不亚于一部哲学论著。
尽管对艺术推崇备至,亚里士多德在写作上却没有像柏拉图那般娴熟地运用文学技巧。我们至今保存的他的那些著作,很多都是来自他自己的笔记或听他的讲座所做的笔记,因而很不完整,这也部分地说明了他的著作难懂的原因。不过这些著作所包含的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足以说明我们为了解其观点而读其内容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亚里士多德把所有的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文学、绘画和雕塑,都看作是一种再现。不过他认为诗歌再现的并非现实世界,而是现实世界中可能存在的事物。这种强调把再现可能性作为艺术创作对象的做法是亚里士多德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他积极平价艺术价值的重要原因。
亚里士多德同时认为,艺术因其具有“再现”的特征,让我们从中获得了快感。因为再现的东西有别于现实,所以我们才会欣赏艺术作品;如果艺术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反而令我们厌恶。想象一下,假使俄狄浦斯刺瞎双眼后再次登上舞台会是一种什么效果。
虽然面对这种真实的场景我们会退避三舍,但当我们沉浸在索福克勒斯的这部杰作《俄狄浦斯王》中时,我们从戏剧再现中获知俄狄浦斯的命运,从而获得快感。亚里士多德强调艺术对公众的教化能力,这一点成就了他的艺术认识论。
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中随处可见的一种倾向就是,将互相关联的现象归入同一种中的同一属。这一点突显他的生物学教育背景。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诗学》中他强调各种艺术形式如何因它们的媒介、对象和再现方式不同而各有千秋。这些不同之处区分出了艺术的不同类型。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在他三大著名“批判”之一的《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艺术理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事实上,“审美”一词被普遍运用于艺术哲学,要得益于康德在审美判断范畴内对艺术的探讨。康德的一些更为具体的艺术哲学观点——比如艺术独立于个体的兴趣,形式为审美判断的对象,天才是艺术创造的主体——也一直受到人们广泛的讨论。
康德的艺术理论十分复杂,因为他试图解决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休谟自相矛盾的两个观点中涉及的问题:对艺术价值的判断看似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它怎样才能变得客观于准确?因为康德的艺术理论建立在他对审美判断的认识的基础之上,而他又把审美判断首先运用于自然,所以,我们的讨论必须从审美判断开始。
关于自然的审美判断,比如,夕阳很漂亮,对康德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判断(他用“判断”指精神上的各种认识活动,因此,无论何时我们思考,我们都在进行判断)。判断出某物漂亮并不会像经验判断(比如,西下的落日染红了云彩)那样增加我们对该物的了解。我们要表达的似乎是对某物的感知让我们发生了某种变化。当我说夕阳很漂亮时,我指的是夕阳在我心中引起的一些感受,尽管我在这做这一判断时赋予了夕阳一种显然很客观的属性——漂亮。和休谟一样,康德面临这样的问题:对我们主观感受的判断如何才具有客观性和有效性?因为我在说夕阳很漂亮时,我似乎并不仅仅说夕阳吸引了我,而且实际上也在说夕阳的漂亮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
关于这个问题,康德的解答比休谟有所进步。回想一下,休谟以经验推断为基础提出口味判断之所以具有客观性,是因为对象本身具有某些能在所有人内心引发快感的属性。康德认为这一观点无法解释我们的一种普遍看法,即赋予对象美的属性这种做法具有“标杆”的作用:我说某物很漂亮时,我不仅相信你会同意我的说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认为你应该同意我的说法。
在阐述审美判断的客观有效性时,康德指出,审美判断里被概念化的快感是一种特殊的感觉。与吃一只冰激凌产生的快感不同,感知美的事物所产生的快感并非来源于对特定兴趣或欲望的满足。它是一种与私欲无关的快感,是在人们观察能诱发快感的事物时产生的一种感觉。康德认为,这种快感的来源存在于事物的那些只吸引观察者感官的特征里。用他的话说,美的事物的形式促成想象力(即允许我们理解任何对象的精神能力)和知性(即概念化的能力)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相互协调,事物的产生似乎就是为了我们去感知它。正是这些精神能力的自由发挥引发了某种快感。而这种快感让我们产生了“某物很漂亮”的判断。正因为这样,我们发现美的事物虽具有目的性,但却从没有实现任何实际的目的。
审美判断的客观有效性问题可以这样来解释,即美的事物引发的快感是一种只要具有人类那样感觉和认识能力的生物都能体会到的快感。赋予一个事物美的属性的做法之所以是客观、有效的,是因为我们假定所有人都能体验到的一种主观感受的存在。根据休谟的解释,人类在审美快感方面的共同性是凭经验推断总结出来的,因而它不得不包含许多例外。而康德则认为,这种共通性的存在,是因为人类具有相同的思维结构。不过,审美判断并不符合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提出的那些严格的经验知识标准。
康德关于自然美的理论中有许多细节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比如,他提出美的对象与高尚的对象之间的区别,这对于他解释人对自然的审美判断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不过,我们须记住,这只是他艺术理论的开端。他进而讨论了艺术的定义,认为艺术是各种人类活动中的一种——他强调艺术是一种人们自由从事的活动。但是我们今天所称的“艺术”,他称之为“美好的艺术”。美好的艺术是审美艺术的一种,旨在通过展现对象的形式来制造快感。因此,康德从审美判断理论的角度来定义“艺术”:艺术作品就是那些通过形式来制造审美快感的作品。
比起“什么是艺术”,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更为关注“为什么有艺术”。即,比起试图理解艺术与人类文化之其他方面的区别,如与科学或工艺的区别,尼采主要关注为什么又艺术这种东西,其功能之于人类生活又是什么。
尼采对于“为什么有艺术”的回答基于其继承叔本华的衣钵而形成的观点,即,生活本身是可怕的。直面这种真实具有致命性——我们可以轻易将之消灭。因此,尼采认为艺术让生活变得易于承受,也让生活在无意义论面前得以继续。
尽管所有艺术均是对“存在”的恐怖的反应,尼采还是认为艺术有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类型,“梦神阿波罗型”和“酒神狄奥尼索斯型”。在此,他继承了康德和叔本华对美与高尚的区别的衣钵。尼采宣称阿波罗型艺术创造梦境世界,那是一个阻隔存在的恐怖的理想境地。其例证便是被尼采视为人类生活之理想化的希腊雕塑,黑格尔也如是说,尽管他们对其平价各执一词。
尼采将阿波罗型与康德和叔本华描绘的显像的个体化世界联系起来,个体在此非常的自在。相反,狄奥尼索斯型却将个体灌醉消融。要了解尼采在此所指为何,可以想象自己参加摇滚音乐会时完全沉浸于音乐时的感受,所有观众摇旗呐喊、融为一体。此刻,尼采认为,通过促使我们拒绝个体化并与控制整个宇宙的力量合成一体,艺术拯救了生活。
尼采眼中的这两种艺术趋势各不相同,但也密切相关。两者互为动态张力。阿波罗型艺术的成就只有在被看成是对狄奥尼索斯型艺术的有意阻滞时才能得以理解,反之亦然。尼采对于梦神阿波罗型和酒神狄奥尼索斯型艺术的区分最终超越了他最初对艺术的考虑,具体地说,即超出了希腊悲剧的范畴。对他而言,两种艺术趋势指示着更为广大的文化力量。
因此,他揭示了阿波罗型否定生活这一总体趋势的面纱;相反,狄奥尼索斯型肯定生活之恐怖。尼采脑中的这种二分法成为了批评的基础,席卷欧洲文化——不仅席卷了它的艺术,也涉及了从科学到道德的各个方面。尼采认为西方的唯一希望在于狄奥尼索斯的重生。
尼采关于艺术以及更为广泛的文化观点在欧洲大陆思想界影响甚广。一段时间里,尼采甚至曾被视为法西斯主义的鼻祖而遭到忽视。如今,他却被公认为19世纪末期的大思想家之一。
文章内容转自一点儿艺术《28位哲学家谈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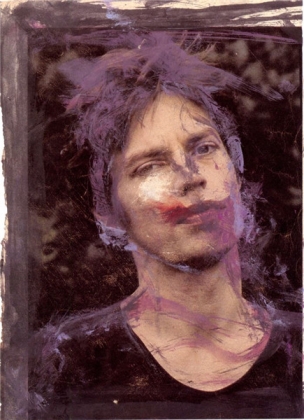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